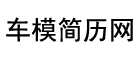宋远升/口述
严慌慌/撰文
我叫宋远升(@用户荆棘鸟),70后,出生于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个小山村。我自小爱看书、学习好,无奈家中贫苦,因为交不起每学期15元的学杂费,初中二年级便退了学。
告别校园后,我在采石场搬过石头,下过铁矿、进过煤窑,吃过的苦头数不胜数。18岁那年,我在井下亲眼目睹工友被石头砸中后当场殒命,这件事警醒了我,让我意识到靠苦力改变命运太难,再这样下去命都可能丢掉。
辞去煤窑的活计后,18岁的我揣着几百元存款重回初中。这个如今看来有些莽撞的决定,把我带到了人生的快车道上,使我从矿工一路逆袭成为大学教授。
靠知识改变命运之前,我曾捱过很长一段时间吃不饱饭的日子。我的老家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,那里稀稀落落地住着四五十户人家。
由于山里灌溉收割不便,小麦不好种,村里人吃不上细面,大都以红薯、玉米、高粱这类粗粮为生,收成也很有限。记忆中,我们家总在为填饱肚子发愁,父母很少有眉头舒展开的时候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,为了逃避饥饿,爷爷带着全家前往东北垦荒,由于奶奶患有哮喘,难以忍受东北冬天的严寒,一家人又回到山东,如此反复过三次。老话说“搬家穷三年”,在东北和山东间来回迁徙,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当我们家最后一次从东北搬回山东,已经是1980年,那时我6岁,家里除了三间破屋再没有其他东西,成了村里垫底的一户。
最困难的时候,母亲只能去邻居家借粮食,后来只带回来一堆发芽变质的红薯,还如获至宝。母亲将红薯削皮、晒干后磨成粉,再烙成红薯干煎饼,吃起来味道苦不堪言,时隔多年我都难以忘记。
我父母都是老实人,父亲上过三年学,母亲从未踏进学堂的门槛,俩人一辈子只知道勤勤恳恳地种地。受限于眼界,他们从不关注我和姐姐的学习如何、考试第几名,只关心我们是否挑好了水、捡完了柴火,甚至禁止我看借来的旧书,认为这是不务正业。
而我天性热爱文字,无论父母如何反对,总是逮着空儿就四处找书看。当时家里有本半文言文的《三国演义》,生僻词不少,但愣是被我翻烂了边儿。
没书读了,我就去附近一户有古书的人家借阅,或者找同学求书看,哪怕是一本连环画。有时在路上看到一角破报纸,我都会万分珍惜地捡起来,读得有滋有味。
或许是闲书看得比同龄人多,或许是我本就有些学习的天赋,读小学期间,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,作文更是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。
可惜成绩带给我的快乐,不足以抵消家贫带来的困苦。我每个学期只能买一个写字本,四五十页根本不够用,为了能多写点字,我总是把字写得很小很密,正面写完反面写,写到自己都难以辨认了,还要继续找空儿写。
进入初中后,不要说学习用品,我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。学校离家有4公里山路,凭脚力得走上个把小时,我只得寄宿,每三天回一次家。每次出发去学校时,母亲会在我书包里塞一二十个地瓜干煎饼,作为未来三天的口粮。
对于青春期正长身体的我来说,一天几个煎饼压根不够吃,总是饿得发昏。夏天天热,煎饼还容易长毛,我不得不把它们晒干,再掸毛,泡一遍水,就着咸菜囫囵咽下。
家里就这条件。我对此也无法抱怨什么,我在学校还有实实在在的煎饼吃,父母若是碰上雨天不干活儿,他们也就随便做点稀饭对付了事。
读完初二,当我伸手向父母要下学期15元的学杂费时,他们脸上露出了难色,那副表情看起来甚至有些不悦。在他们看来,读书未必是条好出路,毕竟村里连一个大学生也没有,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挣钱来得实在。
我当时脸皮薄,一会儿交不上学费、一会儿吃不上饭,还是班里唯一一个拿布条当裤腰带使的男孩,在同学间着实有些丢面儿,便想着干脆辍学得了。
对于我的辍学决定,父母默认了,因而手续办得很顺利。我将学校的衣物、书本拿回家,没多久就上邻市枣庄去投奔爷爷奶奶。爷爷脑子活络,从东北回到山东后一直在尝试做些小生意,彼时他正在枣庄兜售自己种植的旱烟。
在爷爷那儿住了三个月后,我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——在枣庄大柏庄卓山铁矿搬运铁矿石。矿区共45名工人,还不满15岁的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,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。
矿场的工作看上去并不难,我只需要转运被炸开的矿石。但实际上,这份工作相当危险,运矿车的轨道左侧没有护栏,一米多远的地方就是百丈悬崖,下坡过程若有不慎,很可能因为惯性连人带车摔下去。
每天天不亮,我就要出发去半山腰的工地,天擦黑才能回家,总是累得脑袋空空。可我丝毫不后悔辍学的决定,在矿场,一个月100多元的工资终于能让我吃饱饭了,甚至可以一顿吃上五六个细面馒头,这在我读书的时候是绝对不敢奢望的。
日子久了,我便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。虽然年纪小,但我深知兜里有钱才能独立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干了不到半年,我又托在煤矿挖煤的三叔给我找了份下井的活儿,在那里连续干满30天就能拿到300元。
井下工地在地面下两三公里处,从矿道下去时,高的地方能走,矮的地方只能爬进去。一路上不仅要注意脚下的水,还要提防顶棚随时可能掉落的石头,可谓如履薄冰。到达工地仅仅是第一步,接下来我还要在不到半米高的采煤面上斜卧着掘井,一天要干八个小时。
我那会儿还是年轻,听说过瓦斯、冒顶这些灾难,心里并不太害怕。或者说,人在穷困的时候,对金钱的渴望已经超过对危险的恐惧。
大概是上天为了惩罚我这无畏的心性,一个冬天的清晨,我在上井时不慎将右手放入吊车急速上升的铁缆中,三根手指顿时失去知觉。矿上一位负责人急忙用自行车载我去医院,医生将其中两根手指草草包扎,将受伤最严重的中指进行了最经济的截除手术。
随着中指的缺失,我的第二份工作也走到了尽头。那会儿年纪小,没想过要找煤矿索赔,就这样怀着满肚子的悲哀回到了爷爷奶奶在枣庄的住处。见我满脸煤尘,手上又挂了彩,两个老人别提有多心疼了。
养伤期间,我听说同村有人在南京采石场工作,每月能挣400元,心动得不行,等到右手能使上劲了,便立马跑去南京。
在南京泉水采石场,我仍然从事重体力劳动。烈日炎炎之下,16岁的我要将爆破后散落在山坡的巨石装车,再送到远处的碎石机中粉碎。石块又重又锋利,我怕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被磨破,每天赤膊上阵,身上时常被划得鲜血淋漓,新伤旧伤层层叠叠,仿佛一枚枚勋章。
对年少的我来说,累点、苦点都没事,只要有钱挣就好,可月底一发工钱,心里凉了半截。原来大家口中的一个月400元,只是针对那些最能干的工人,像我这样年少体弱的,到手能有个200元算不错了。
我曾以为靠打工可以改变命运,一晃三年过去了,累死累活,还失去了一根手指,身上仍然只有几百元存款。辍学以来,我第一次有了深深的疲惫感。
正郁闷的时候,我又听人说村里有个小伙子20年前去吉林下煤窑,后来在那里安了家,日子过得不错。这个消息让我再次看到希望,决定去吉林碰碰运气。
我背着铺盖卷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,最后也没打听到那位老乡的下落,但如愿进了吉林蛟河奶子山煤矿,那里工资确实高,一个月能开600元。
因为此前有过下煤井的经验,我再回到煤井适应得很快。和以往不同的是,这次我随身带着借来的初三课本,每天下工后,都会拿起课本自学一会儿。刚开始,同住的工友会笑话我说看这个有啥用,我也被问得语塞。是啊,有什么用呢,靠几本破书就能扭转命运了吗?但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出路了。
打工的日子波澜不惊,我以为接下来几年也会这样继续下去,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场意外,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那天,我和工友井下在工作累了,便停下来休息,班长坐在我不远处抽烟。突然间,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从他上方落下,灾难来时毫无征兆,班长来不及闪躲就殒命西去。
时隔多年,我仍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一幕对我的冲击有多大,当我缓过神后,我当即决定要换一种活法。班长的意外遇难让我切身体会到,在这里多待的每一秒都是听天由命,我怕自己有命赚钱,没命花。
我很快离开了东北,走之前花三百元给自己买了双皮鞋和雪花牛仔外套,作为对自己打工几年的奖赏。回到家里时,我身上还剩下600元,那便是我这四年全部的存款了,我打算用这笔钱来供自己读书。
和当初辍学一样,听说我要复学,父母表现淡然,不支持也不阻挠。在外打工的这几年,我也习惯了自己做决定,懂得自己对自己负责。我想趁年轻赌一把,赌输了,大不了再回工地干活。
1992年春节刚过,我直奔初中,找到了当年颇赏识我的语文老师,他此时已经升任校长,爽快同意了我的复学申请。当初离开时,我因为家贫在同学间抬不起头来,继而对学校产生了排斥,觉得这里不能给我光明的未来。在外颠簸流浪四年,当我重新回到学校后,内心竟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
坐回初中教室,端起书本,我才明白这样的平静有多珍贵。在工地苦干一辈子未必能致富,但在学校苦学的每一分钟,似乎都让人在成功路上更进一步。
辍学近四年,要考上高中绝非易事,我深知自己没有试错的空间,不成功便成仁,所以只能玩命学习。每天晚上,别的同学都沉入梦乡,我还在教室就着煤油灯熬到凌晨,因为吸进了煤油烟,鼻孔周围总是黑乎乎的。
我自己也觉得意外,四年的高强度劳动不仅没有让我的大脑变钝,反而像开窍了一般,比退学前吸收知识更快、学习起来也更轻松。
再加上足够的专注和努力,很快我就把从前落下的知识捡了起来。那年中考结束,我们学校共有四个学生考取了重点高中,我便是其中之一。
得知我考上重点高中的消息,父母依旧麻木,倒是堂姑和已经嫁人的姐姐很为我高兴,她俩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定期资助我生活费,让我免去了后顾之忧。
堂姑是乡里远近闻名的能干农妇,从前我们关系平平,但自从我考上高中,她便对我像亲儿子一样关心,希望我能发挥才学,成为宗族的荣耀。
读高中期间,我在学习上的潜力再度展现出来,高一我还在年级十几名徘徊,高二就次次前十,高三更是从未掉出过前三名,乃至被同学们封了“考神”的称号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不是真的智力超群或是什么考神附体,不过是四年苦难磨练了我的心智。只要不再回到烈日炎炎的矿场、黑暗的井底,学习再苦再累,于我也不过是“挠痒痒”罢了。
1995年高考,我稳定发挥,以高分成为兰陵县文科状元。我打工攒下的600元也花了个精光,身上一文不名,但我赌赢了。我知道,苦难已成过去,上天终会嘉奖不认命的人。
我成为状元的消息很快炸开了锅,乡里乡亲全跑来祝贺。我很开心,不仅因为我得以摆脱父辈的命运,更因为我初步证明了读书的价值,我在大家眼里看到了羡慕。
大学期间,堂姑和姐姐在自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,每年都极尽所能地给我凑部分学费,还时不时给我一些生活费。
如今想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,那会儿家里那么穷,学费也得靠亲戚资助,我内心却有个要出国留学的执念。大学四年,我成天抱着厚厚的英语词典背,背过了不算完,还要将每个单词抄写50遍,后来的英语四六级考试都是一次性通过。
1999年我大学毕业,正好赶上国家包分配的末班车,被分到兰陵县司法局当了公务员。在老家人看来,能端上铁饭碗是一份好得不能再好的差事,我却不太甘心,花几个月时间考下律师资格证后,便辞去公职,在临沂做了三年律师。
和当初打工一样,在临沂的三年,我始终不满足于现状,总觉得地方太小不够我施展拳脚,还想往更大、更远的世界跑,于是报考了华东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。
读研第二年,为了圆当年的梦,我申请了留学比利时根特大学。申请主要看英语成绩,我大学的努力这会儿终于派上了用场。托福满分677分,我考了639分,是华东政法大学那年去留学的四个人中分数最高的。
留学比利时的花费高达十几万,最开始我身上只有三万存款,缺口巨大。后来还是20个亲友给我凑够了这笔钱,其中堂姑通过贷款借了我四万元,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深深感动。
在国外的一年,是我真正开拓眼界的一年,也是我无比充实的一年。我不仅在上课之余去了法国、荷兰、卢森堡、德国、埃及这些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国家游览,还利用国外的资料,写了一本法学著作,越来越向学术之路靠拢。
2006年,我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,留校做了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杂志的编辑,这本杂志是我国公开发行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期刊,编辑岗位归属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教辅编制。工作一段时间后,我因为不想一辈子做教辅,又去考了复旦大学的法学博士。
2010年,我博士毕业,成功入职华东政法大学,成为一名法学讲师。期间出版法学专著18本、法学论文110余篇,作品字数超过500万字。凭借过硬的学术成绩,我在入校七年后便被评上教授,当上了硕士生导师。
如今人至中年,我的步伐总算慢了下来。从前打工也好、学习也罢,我都是个不甘现状的人,总爱往前冲,现在却越来越喜欢回味过去,品味之中,也对过去的苦难多了一份理解和感激。
童年时期,父母经常因为贫穷吵得不可开交,我始终笼罩在饥饿与争吵中,说对他们毫无怨言那是假的。很多年后,我才明白了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的道理,对他们有了体谅之心。如今,父母在村里抬头挺胸,过着安稳富足的晚年,是我作为儿子最大的满足。
能够走到今天,我堂姑和姐姐功不可没。尤其是堂姑,我每次回家都会看望她,就像她当年拿我当儿子对待一样,我也拿她当父母一样的恩人,礼物永远买一式两份,父母一份,她一份。
对姐姐的感谢自不必言,她不奢求我的回报,我只能更加疼爱她的孩子,去年外甥结婚,我给了一个五万元的红包。
我的求学经历也影响了老家的许多孩子。以前我们村的成年人大多不重视教育,大家伙儿不看谁家孩子成绩好,而是看谁家孩子捡柴火厉害,现在不一样了,每次我回老家,都会有父母让孩子跑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。
我是一个念旧的人,这些年会不时回到从前的工地转一转。触景生情之下,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太阳底下暴晒、被石头压弯了腰的自己。每当这时,我都无比感激自己复学的决定,好在我醒悟得不算晚,好在苦难都过去了。
我还是个喜欢寻找生活意义的人,许多事情本身没什么意义,比如我曾遭受过的苦难。但如果苦难所带给我的改变也能对年轻人产生一些激励,它便有了意义。
【本组图文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,严禁转载】
点击@用户荆棘鸟关注本文主人公
点击以下链接,看往期文章
/我,海归,从小爱美,25岁差点丧命,坚持化妆打扮,成为美妆博主/
/我,北京人,当过车模和舞娘,曾是中学老师,现在加拿大教人玩枪 /
/我,初中学历,在深圳炒房暴富,曾拥有18套房,经历过一夜破产 /
#自拍我的故事#【本组图文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,严禁转载】以上是@用户荆棘鸟分享的真实经历。如果你或者你的身边有不得不说的故事,请点击“私信”告诉我们。